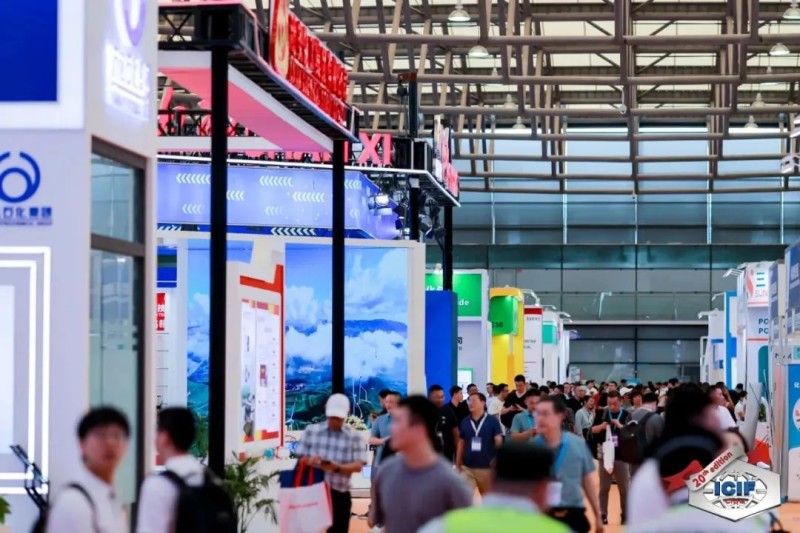编者按
青年,不止是年龄,而是一种心境与精神。106年前,以青年为先锋的五四运动于民族危难之际爆发,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穿越世纪风云,一代代青年们在强国建设的征程上接续奋斗,一代代科技工作者秉持着科学家精神笃行不怠。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我们特推出“他们正年轻”系列稿件。面对青春困惑,看老一辈科学家如何做出人生的重大选择;面对科学难题,看青年科技工作者怎样勇攀高峰。
五四从未远离,青年永远在场。
青春,是一段充满无限可能的时光,却也往往伴随着迷茫与困惑。青年科技工作者在科研道路上,会对研究方向感到迷茫,会对努力得不到回报感到沮丧,会在面对科研瓶颈时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会有同侪压力、年龄焦虑等等。这些困惑,就像一层厚厚的茧,将青年人束缚其中。
然而,当我们回望那些为我国科技事业倾尽心血、做出卓越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不禁感慨,在曾经物质匮乏、条件艰苦的年代,他们是如何从迷茫与困顿中突围而出,做出正确的选择呢?
选择:用家国情怀充盈人生价值
1952年,新中国首次高考启动。欧阳自远没有追随自己的文学爱好,没有定向于自己最感兴趣的天文学和学得最好的化学,也没有遂家人所愿去学医,而是选择学习矿产资源勘探,去“唤醒沉睡的高山,献出无穷的宝藏”。表面上这是一次与各种期望背道而驰的决定,实则透露出朴素深远的家国情怀。
中学时代的地理老师袁家瑞曾对欧阳自远说过:“我们拥有‘地大物博’,当你怀着强盛国家的心去学习的时候,你的学习就会悄然转向热爱……”这些话如重锤击碎迷雾,让欧阳自远对学习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原来的读书改变命运,转化为学习报效祖国。
同样是在1952年,曾庆存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入学后被建议改学气象专业。今天看来这或许是被调剂的无奈,但在当时,这一调整其实反映了国家与个体之间更为紧密的联结。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曾庆存(右)与同学在苏联留学。
图源:中国科学报
新中国刚刚成立,抗美援朝、农业生产、基础建设都对气象科学提出了迫切需求。一场晚霜让河南40%的小麦颗粒无收,出生于农家的曾庆存真正意识到,天气预报与粮食安全、民生福祉大有关联,科学不仅是抽象的理论追求,更是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支撑。“为了国家需要,让我们学什么我们就去学什么!”
欧阳自远最终将“北京地质学院”写进高考志愿的那一刻,曾庆存下决心到了气象专业就好好儿学、好好儿干的那一刻,不只是个人选择的转折,更折射出那个年代科技工作者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
定向:在时代浪潮中锚定个体坐标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做出抉择,历来是个人成长路上的一道关卡,不管是在国家发展的初期,还是在经济转型、技术发展与个人命运交织的关口。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1993年12月,刘嘉麒在南极长城考察站。
图源:新华社
刘嘉麒在1981年面临的抉择切身而具体。当时他刚从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硕士毕业,被原单位领导力邀回去工作,并许诺回去后可以分房和升职。这种现实诱惑,对于年近四十、渴望安定生活的人来说,分量可想而知。他一度动摇,但最终做出了清醒的选择。
刘嘉麒认识到自己更适合科研而非仕途,与其在官场周旋,不如在岩石前坚守真理,继续行走在远离喧嚣的学术路上。他的自觉与坚持,为后来中国地质与火山科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而珍贵的基础。他通过实地勘察一座座火山,攀登了人生的大山、科学的高峰。
赵忠贤是我国高温超导研究的主要倡导者、推动者和践行者。二十世纪90年代,国际物理学界在高温超导研究上陷入瓶颈,相关领域迅速降温,但赵忠贤和团队却选择了逆势而行。他们坚持实验、制备、观察、失败、重来,周而复始。“热的时候坚持,冷的时候更要坚持。”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1992年前后,赵忠贤在实验室工作中。
图源: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这种近乎执拗的坚守最终换来了2008年团队将超导临界温度提高到50K以上的突破,创造了55K的铁基超导体转变温度的世界纪录。真正的科学进步,往往诞生于寂寞岁月中的不懈坚守,而不是追名逐利的热闹非凡。
在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中,诱惑与喧嚣从未缺席,变革与焦虑也从未远离。真正能走出自己道路的人并不随波逐流,内心深处早锚定了自我坐标。前辈科学家在中青年时期面临时代与行业的挑战,认清自己适合做什么,看透行业的发展前景,在纷乱之中坚持,在孤独中前行,用一生执着丈量出属于个人也属于科技发展的宽广版图。
转向:在突破自我中开凿生命价值
科技工作者面对创新的巨大挑战,无疑会有无数个自我怀疑的瞬间、得失权衡的煎熬。在深耕各自的专业领域时,前辈科学家也曾经历诸多艰难时刻,需要角度或大或小的转型,他们选择勇敢直面挑战。
欧阳自远从地质学跨界到航天领域,本身就蕴含着一种时代隐喻。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升空,引发了世界科技格局的剧烈震荡,也激发了这位青年地质学家对陨石与太空的浓厚兴趣。他在1976年吉林陨石雨的研究中崭露头角,并逐渐将研究领域扩展到了太空,花甲之年又选择了新的跃迁,投身探月工程。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1978年,欧阳自远研究月球岩石样品。
来源: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毫无疑问,从低头看地到抬头望天,对欧阳自远来说是一种全新的突破,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破茧而出。他用半生时光完成精神蜕变,从被动接受命运馈赠的“矿石”,到主动雕琢宇宙谜题的“匠人”,点点滴滴的前进与转变,最终汇聚成“嫦娥”系列卫星划过太空的壮美轨迹。
曾庆存的转型,不仅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也成为学科突破的重要注脚。二十世纪60年代他提出“半隐式差分法”,首次实现用原始方程直接进行天气预报,推动了气象学预报技术的实质性进步。这一方法至今仍在实际预报中广泛应用。
然而,他并未停留在已有的成果之上。二十世纪70年代,为响应国家需求,他毅然离开了熟悉的数值天气预报领域,转向卫星气象和大气遥感这一全新方向。在完全陌生的领域中,他以巨大的学习和工作强度,完成了30万字的《大气红外遥感原理》专著,为国际卫星遥感定量理论和我国首颗自研气象卫星奠定了基础。他的两次主动转向,不只是技术路径的变化,更是对科学家精神和国家使命感的生动诠释。
在时代的需求面前,真正的科学家从不困守一隅,他们以自我突破回应时代命题,在不断变动的世界中,锚定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与价值。在时代浪潮中,真正的突破也从来不只是顺流而上,更是个体锚定自我坐标后,主动迈出的那一步。从脚下泥土到浩瀚星空,从头顶风云到苍穹遥感,正是这样一次次勇敢的跨越,成就了科学与精神的双重飞跃。
启示:在选择与坚持中淬炼精神之光
回望前辈科学家的成长轨迹,不难发现,在个人理想与国家需求、现实诱惑与学术坚持之间,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后者。他们的选择并非源自简单的服从,而是深思熟虑后的主动认同:认同国家发展的紧迫,认同科学探索的价值,认同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的深刻交织。他们能一次次做出对国家和人民有意义的选择,体现了那个时代科技工作者对理想信念的坚守与担当。
我们看到的不是被神话的奉献者,而是真实存在过的困惑者与突围者。这些真实的心路历程,比任何说教都更具感召力——它告诉我们:科学家精神不是圣徒式的苦修,而是每个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校准人生坐标的勇气;科技报国不是抽象的口号,是具体而微的生命选择在历史长河中的持续共振。
当五四的钟声再次敲响,愿当代青年科技工作者能看见这些穿越时空的破茧之光——不必害怕理想与现实的温差,不必焦虑成长的速度,因为所有伟大的蜕变,都需要时间的淬炼。就像欧阳自远手中的陨石标本,经过星际穿越才拥有独特的纹路;就像曾庆存解析的气象云图,穿过万千褶皱才呈现清晰的轨迹;就像刘嘉麒研究的火山岩,历经地心烈焰才铸就坚硬的品格;就像赵忠贤团队刷新的高温超导纪录,20年把冷板凳越坐越热。
去触摸科学的温度吧,在困惑中保持对未知的好奇,在迷茫中坚守对真理的信仰。当你在实验室的深夜抬头,看见窗外的星空时,请相信:每一颗在青春里努力破茧的灵魂,终会成为照亮人类文明的星辰。
作者|观沧海 资深媒体人
审读专家|尹传红
科普时报社社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