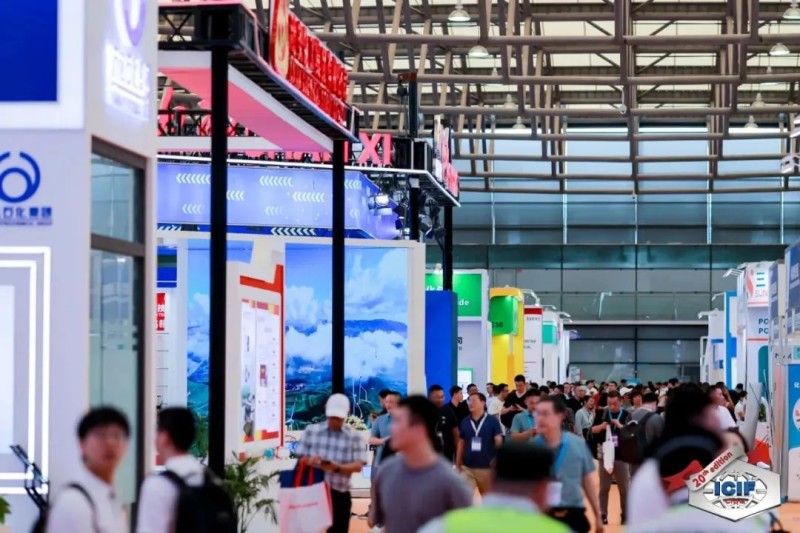前文我们讲了魏文侯礼贤下士,对卜子夏和田子方执弟子礼,还对段干木这位隐士行礼。今天我们来看魏文侯的诚信,这也是魏文侯打造完美人设的重要一环,治理国家诚信当然非常重要,但儒家和法家对此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正是因为这种差别,在一段史料的取舍上,司马光的倾向很值得留意。
《资治通鉴》中的原文为:文侯与群臣饮酒,乐,而天雨,命驾将适野。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无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
说这个魏文侯与大臣们饮酒,气氛很愉快。虽然外面下起了雨,但是室内举办的酒会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忽然魏文侯要人准备马车,说要送自己到野外去,身边的大臣都来劝告,喝酒喝得正开心,外面又在下雨,您何必非要赶在这个时候出门呢?魏文侯给出的理由是:我已经和管理山泽的官员约好了,这个时间要去打猎,我怎么能让人家白等一场呢?
下雨天当然没有办法打猎,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魏文侯如约赶到了约定地点,亲自告诉那位管理山泽的官员,取消当天的打猎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资治通鉴》的这段记载源自于《战国策》,只在文字上做了很小的修改。在《战国策》的版本中,最后还有一句议论说魏国从此走上了强国之路。但是这样一件小事为什么值得《资治通鉴》记录在案又为什么会被《战国策》当成魏国走向强盛的起点呢?
熊毅老师认为,以如今的眼光来看,首先魏文侯不够聪明,当初做约定时如果说好了遇到下雨就自动改期,也不会有后面的麻烦。其次就算没有预先约好,也犯不着亲自跑去通知,一切都可以按照管理流程来走,管理山泽的官员被称为虞人,级别很低,魏文侯亲自跑去通知虞人,那就相当于集团公司董事长亲自去通知某个分公司里的某个科长,这不是很荒唐吗?如果魏文侯是一个高明的管理者,就不可能做得这么荒唐。
那唯一合情合理的解释就是魏文侯在演戏给大家看,他就是要在所有臣僚的面前演这一场戏,让所有人目睹自己对信用有多么看重。虞人是小官,打猎也是小事,领导对小官和小事尚且如此守信,何况对高官和大事呢?这层道理精通谋略的《韩非子》早就揭穿过了。
对于魏文侯和虞人的故事,《韩非子》最可恨的就是把它当成论据,来证明“小信成则大信立”的道理。这个道理貌似很正确,也很磊落。讲信用嘛,直到今天也是美德。如今我们拿征信记录去银行贷款,征信记录越干净,贷款审批就越容易。只要平时信用卡还款及时,交话费、还房贷从不逾期,就可能从银行获得大额贷款,这不就是“小信诚则大信立”吗?如果连小信都不成,大信就绝对立不起来。
儒家当然不反对这种道理,事实上孔子亲口强调过信用的重要性,比《韩非子》说的更甚,当时子贡向孔子请教治国之道,孔子教了三大注意事项:第一,粮食储备要充足;第二,武器储备要充足;第三要获取人民的信任。这三件事情的重要程度并不相同,信任最重要,粮食在其次,武器排在最后。为什么这样排序呢?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意思就是说,虽然没有武器会被杀死,没有粮食会饿死,但死人的事情自古以来屡见不鲜,不是多大个事儿。只要大家对君主的信任度还在,政权就不会垮。
司马光很信任这套理论,在他看来朝廷凡是说到的就一定要做到。这是儒家对诚信的看法,把诚信当做立国之本。而《韩非子》讲的诚信是法家版本的信用,把诚信当做权谋和手段。所谓“小信成则大信立”在权谋和手段的意义上,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庞氏骗局。先成小信,在集资时候承诺要给多高的利息,在分红时就真的给了多高利息,一分都不少,等大家都尝到了甜头,产生信任投入更多的钱,集资人就揣着巨款消失不见了。
《资治通鉴》第 107 卷收录的东晋时期徐邈写给范宁的一封信,徐邈在信里说范宁不该派人到民间去打听老百姓对官员的评价,因为自古以来凡是愿意说长道短的,愿意给别人做耳目的通通都是小人。这些小人的特征,就是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借小信而成其大不信。
儒家政治对这种事相当忌讳。法家重视诚信,是因为其最核心的管理技术是赏罚制度,而赏罚必须以诚信为基础。这正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关于魏文侯和虞人这段历史记载取《战国策》而不取《韩非子》的原因。
这就好比父母管教小孩子,儒家的办法是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传,在这个基础上,不对小孩子失信。而法家的办法是设立明确的赏罚标准,不管小孩子能不能明白道理,反正做对了就奖,做错了就罚。一旦该奖不奖,该罚不罚,约束力就失效了。
法家的赏罚重点就是标准清晰明确,至于在不在情合不合理,被惩罚的对象能不能想得通都不重要。那么问题来了,讲诚信难道还可以,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吗?确实可以,在法家看来不是问题。
《韩非子》讲过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例子。魏文侯手下的一位干将李克。他在做地方官的时候,很想提高当地人的射箭水平,就下了一道命令,说凡是有打不清的官司,一律让当事人射箭定输赢。谁能射中靶子,谁就能赢官司。这条命令下了以后,当地人就开始没日没夜地苦练剑术。后来和秦国打仗,李克这边赢得很轻松,因为民众个个都是神箭手。
李克确实做到了赏罚分明,显然也很讲诚信,以箭术决定官司的输赢,标准清晰明确。唯一的缺点就是太不讲理了,诚信竟然可以和讲理完全割裂,这在现代人看来难以置信,但从法家的角度来看,诚信本来就和讲理毫无瓜葛。
显然司马光无法认同这个道理,更无法认同法家的初心,但他对法家的诚信却也能适度地接受。在《资治通鉴》第 2 卷里,讲到商鞅变法,司马光就拿魏文侯和虞人的故事举过例子,说虽然魏文侯不属于儒家意义上的标准贤君,商鞅是一个以刻薄寡恩著称的人,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更是一个拼武力、比诈术的时代,但他们依然会用诚信来统治国民,所以当今天子更应该明白诚信治国的重要性。
问题是,道理虽然简单,但真正落实到操作层面,“小信”和“大信”的关系其实很难处理。
《资治通鉴》第 105 卷讲到著名的淝水之战,前秦皇帝苻坚惨败,国内人心离散。大将慕容垂申请带兵到北方平定骚乱,苻坚同意了。权翼劝苻坚说:“在这种国家新败、人心惶惶时,正应该召集名将,把他们安置在京城,您怎么反而放慕容垂离开呢?慕容垂是何等的英雄豪杰,您这不等于放虎归山吗?”苻坚的回答是:“我都已经答应他了。普通百姓尚且应该说话算话,何况天子。”
苻坚很讲诚信,而讲诚信的结果是身死国灭。
如果魏文侯遇到这种境况,会坚持原则呢?还是会随机应变呢?
在法家思维里,小事必须讲诚信;大事就看情况了。
魏文侯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诚信在不同理念中有不同呈现。儒家将诚信视作立国根本,司马光也极为认同,认为朝廷必须言出必行,如此方能凝聚民心。法家虽把诚信当作权谋手段,但也重视其在赏罚制度中的基础作用。魏文侯对虞人的守信,无论是作秀还是真心,都引发了我们对“小信”与“大信”关系的深度思考。在现实里,我们面临诸多类似抉择,不能盲目守信,而应像司马光所倡导的那样,以儒家的诚信理念为根基,同时借鉴法家合理之处,审时度势地践行诚信。只有这样,才能在个人品德修养、社会人际交往乃至国家治理等多方面都能妥善应对,既坚守诚信的底线,又能灵活处理各种复杂状况,让诚信真正成为推动个人进步、社会和谐、国家繁荣的强大助力,而非羁绊手脚的绳索,从而书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诚信华章,传承并发扬诚信这一历久弥新的宝贵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