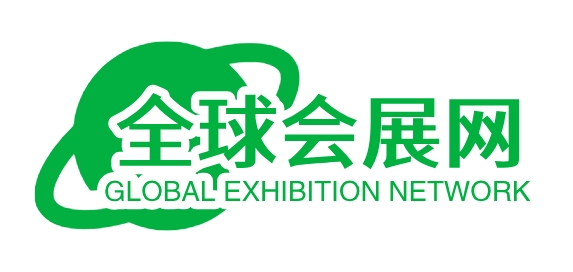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接连下了几周的雪,世界早就被覆盖上了一层厚厚的冰霜,太阳出来,一道道金光划破天际,在地面上开辟出一条条小道来,向阳面的冰霜开始消融,涓涓细流汇聚到地上不一会儿就被黑色的土地吸收掉了。
丰缘山的向阳面,有一堵坚实的雪墙,随着“啪嗒、啪嗒”的声响,雪墙裂出一条缝来,随后“轰”的一声巨响,惊得树上的鹞鹰扑棱着翅膀飞走了。
雪墙倒塌的地方赫然出现了一个三丈宽的圆形坡面,竟是一个宽大的洞穴,洞穴有数丈深,一眼望不到底,光线被旁边的耸立的针叶林遮了起来,黑黝黝的,有些隐秘。
里面传出来一些窸窸窣窣的声音,不一会儿从洞穴里走出来三个人,两名佝偻着身子的老者和一个穿着褐色棉衣的青年。
“看来我们活下来了。”一位穿蓝色袍子的老者说。
“是啊,没想到是我们活了下来。”另一位瘦削如骨的老者说。
“爹爹,项前辈,韩某自知罪孽深重,我会去官府自首,将这一切公之于众的。”青年面露忧色,故作镇定地说道。
“秋阳,此事你也不是非要为之……”瘦削老者说,“况且无人知晓。”他说完看了看蓝衣老者。
“是啊,是啊,韩贤侄,这都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况且令尊还需要你养老送终……”蓝衣老者诺诺开口。
“孩儿,阿祥走了,为父……为父……只有你一个孩子啦。”瘦削老者说着顾自抽泣起来。
“爹……”韩秋阳轻声叫唤一声,“诶,我心意已决,当日情形历历在目,已成心魔,这些天我也是苦苦挣扎才做出这个痛苦的决定。”
不再有人说话,只有凛冽的寒风呼啦啦地吹得树枝乱颤,斗大的霜雪摔落下来重重地砸在地上,发出一声声的闷响,在留下脚印的小路上开出一朵朵肮脏的花朵。
远处传来劈劈啪啪的声音,韩秋阳停下脚步来,竖起耳朵,那是马蹄踩在薄冰上发出的声响。渐渐声音近了,是一队官兵,骑在瘦马上的是便是云阳县县令陈光,他穿着青色官袍,面容苍白忧郁,眉宇间透着一股浓烈的哀伤。跟随在他左右的是六位衙役,走在队伍后边的两位衙役拉着一辆独轮车,上面放着一团用麻布包裹起来的东西。
“汝为何人?”一个衙役看到韩秋阳一行高声问道。
“大人,”瘦削老者连忙跪下,“我们乃是云阳县村民,因遭雪灾,逃难去的。”
陈县令摆了摆手,示意他起来,他翻身下马,围绕着几人转了一圈,把目光锁定在韩秋阳身上,疑惑地盯着韩秋阳,不停用手捋着定居在下巴的胡须,神情渐渐凝重起来,周围异常安静,没有人敢说话,只有轻微而急促的呼吸声此起彼伏地震荡着空气。
“你?”陈县令说。
“大人!草民有罪!”韩秋阳没等陈县令说完便扑通一声跪下了。
两位老者面面相觑,不知所措,陈县令也被他的行为怔住了,他飞快地提溜着眼珠子,“你是否有罪自有本官审理,现在我让你认一个人。”陈县令缓缓开口道。
独轮车上的麻布被一把掀开,里面竟然躺着一个人,确切地说那是一具已经被冻僵的尸体——
“阿祥!”瘦削老者惊呼起来,“我的儿!”
陈县令紧皱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诸位,看来我们不必大费周章了,我想这几位肯定会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的,来人呐,把他们都请回府,本官要亲自审问。”
“诺!”领头的衙役说,“快点,你们就随我们回府衙吧。”
云阳县的府衙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冻雪,把青砖灰瓦都彻底覆盖在里面,暗色的楹柱透着淡淡寒气,直让人大腿发抖,一进大门便可看到一座宽阔的大堂,正中央悬挂“正大光明”的描金匾额,青蓝碧绿的墙面彩绘已经脱落了不少,显得沉闷、暗淡,了无生机,韩秋阳镇定地往里走,没有泛起丝毫波澜,只有经过狱神庙的时候,略微停下脚步,踌躇了一会才继续往里走,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府衙后殿的厢房里,陈县令早就端坐在一张黄色太师椅上面,周围站着两名衙役,看起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三个人依次排队站在陈县令的面前,他们一言不发,低着头,似乎在等一个命令。
“你们谁先说。”陈县令缓缓开口,他说着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
“陈大人,草民来讲吧。”韩秋阳向前走上一步,向陈县令行了礼。
“说吧。”陈县令点点头。
“今日陈大人发现的死者乃是草民的弟弟,这是我们的父亲,”韩秋阳说着指了指瘦削老者。
“嗯,这样看,是有几分相似。”陈县令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何惧怕本官,张口就言有罪?我倒要看看是何罪过。”
“大人,草民杀人了,”韩秋阳嘴唇翻动,一字一句地吐出来,“我还把他吃了。”
陈县令听闻倒吸一口凉气,整个人蹭地站起来,“你说什么?!”
“大人!”两位老者慌忙下跪,“事情并非如此,一切都有原因——”
“你们不要讲!”陈县令斥责道,“韩秋阳,你给我好好解释解释!”
“大雪之前,云阳县遭遇了蝗灾,粮食本就收获不多,刚入冬就下了大雪,老百姓的生活毫无期待,路上都是逃荒的灾民,随着粮食缺失和寒冬的摧残,活下来的寥寥无几,路有冻死骨,千里无鸡鸣也已是常态。”韩秋阳顿了顿,眼神悲悯地看了一眼陈县令,“草民的母亲死得早,家中仅有父亲和弟弟两人,为了生存我们倾尽全力备了一些粮食就踏上了逃荒之路。”
“这些本官都知道,汝无需多言,快说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陈县令催促道。
“大人,稍安勿躁,且听草民细细说来,事情并不复杂。”
“那你长话短说吧。”陈县令说。
“草民一家准备穿过丰缘山到洞庭县寻找生路,这一走就遇到了一对兄弟,大的叫杨荣,小的叫杨炳,父亲见其可怜便让他们随我们一起前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傍晚时分,天气骤变,寒风吹得我们睁不开眼睛,一场暴风雪似乎就要来临,为了躲避风雪,我们便在丰缘山上找了一出洞穴躲进去避避风寒、歇歇脚。
父亲是个心善之人,眼瞅着杨氏兄弟没有干粮便把我们所剩不多的翻烧分了一些给他们二人,父亲说,再过两日便可翻过丰缘山到洞庭县了,让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
大雪如期而至,鹅毛般的雪花哗啦啦地飘荡下来,就好像漫天飞舞的白色符箓,看得人心里直发毛,寒风刺骨,父亲建议我们用积雪在山洞口筑起一道厚实的围墙,抵挡住风雪——
我们都觉得有道理,正当我们准备动手筑墙的时候,项前辈也来了,他孤身一人,原是云阳县芝兰村的村医,也去洞庭县避难遇到了风雪,阴差阳错地碰到了我们。”韩秋阳说着用手指了指另一个老者。
“大人,”蓝袍老者说,“草民项观程,确实是云阳县芝兰村村医。”
陈县令看了看他,点点头,“然后呢?”
“我们一行人就这样被大雪困在了山洞里。”韩秋阳苦笑一声,“雪墙挡住了风雪,让山洞里变得暖和了一些,我们六人挤在山洞的角落里歇息,静待风雪过去好赶路,没承想这场雪一下就是三天。”
韩秋阳叹了一口气,“父亲携带的粮食根本抵不住六张嘴巴,在洞穴里我们第一次遭遇了粮食危机。”
“看来这跟吃的有关,想必是为了吃的打起来了?”陈县令问。
“也不全是。”韩秋阳摇摇头,“一开始我们想过冲破风雪的重围,离开这洞穴的,可惜计划失败了。”
“你们的计划是什么?怎么做的?”陈县令问。
“第二天,暴风雪有缓和过几个时辰,草民的弟弟韩祥和杨炳自报奋勇准备去找一条出路,至少也得找一些吃的回来,否则再过几天我们都要饿死在这洞穴之中了。
草民一开始是反对的,但也实在没有办法,于是跟他们俩约定,一个时辰必须返回,事后来看——草民还是太乐观了,两人离开不久暴风雪就噼里啪啦地砸落下来,而草民的弟弟韩祥他们再也没有回来,直到大人巡防发现他的遗骸,我们才,我们才……”韩秋阳说着眼睛里挤满了泪珠,硕大的泪珠在眼眶中打转,翻落下来,晶莹剔透。
“原来是这样,也就是说本官一行发现的韩祥尸骸是这么一回事,看来是风雪太大,他们体力不支随后倒下了。那么,怎么只有一人?不是还有杨炳吗?”陈县令问。
“大人明鉴,他们两人是分头行动的,杨炳跟韩祥是反方向的,大人可以派人去发现韩祥位置的北面查看,应该能找到杨炳。”韩秋阳解释道。
“小五,”陈县令对一位衙役说,“你负责这件事,把杨炳尸体找到来验证一下这个韩秋阳是否如实回答本官的问题。”
“诺!”
“韩秋阳,那么洞穴里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按照你的说法洞穴里面应该还有四人,怎么现在就只有你们三个人了,那个杨荣——你真的杀了他?”
韩秋阳点点头,“确实,草民杀了杨荣。”他说完斩钉截铁地看了看陈县令,眼神中没有丝毫的感情流动。
“那你犯了诛杀之罪,杀人偿命,看来此案也不用审理了,主犯自首,来人呐,把这个韩秋阳押到牢里去。”陈县令闻言,朝着衙役挥挥手。
“大人!”韩父连忙喊道,“冤枉啊,秋阳所言不假,但却有隐情——”
“韩老头,”陈县令站起身来,“你不能补充,你们是亲父子,我们大魏刑律有规定,至亲不得为其申辩,项先生可否有补充啊。”他说完看了一眼项观程。
“回大人,韩老友所言不虚,杨荣之死却有隐情,还望大人耐心听老者给你讲来。”
“准。”陈县令说完闭上眼睛养起神来。
“韩祥和杨炳许久不见回来,又是大雪漫天,我等心中万分焦急,苦于天气实在是恶劣,最终也没有出去找寻他们,只能心中祈祷吉人自有天相,能逃脱这无边雪灾。
过了三日,风雪依旧不见颓势,反而愈来愈烈,韩老友随身携带的干粮已经快要见底,若是如此再过三日所有人都将饿死。
到了第四日,韩老友饿昏了,整个人气息微弱,我替他把了脉,情况不容乐观,如果再不进食,他将彻底失去生命。”项观程说。
“这么说来,你是为了救自己的父亲所以才杀的人?”陈县令看向韩秋阳,“尽管你有孝心,但如此手段实在是残忍一些了,于情本官可以理解,于法难容,实属罪行昭彰,本官绝不姑息!”
“大人明鉴!”韩父喊道,“事情也并非如此,事实上......事实上......这是杨荣挑的头!”
“什么意思?”陈县令皱起眉头,“项老者,你是否还有补充啊。”
“回禀大人,老朽确实还未说完,韩老友所言不虚,整件事情确实是杨荣挑的头。”项观程叹了一口气,缓缓道来。
韩父的气息渐渐微弱下来,他的鼻孔里散发出一股毛糙糙的声音,低沉且痛苦,他闭着眼睛,身体靠在一块湿漉漉的平整岩石上,死神就站着他的面前,只要一抬手便可将他的姓名取走。
“爹爹……”韩秋阳轻声在他耳边叫唤,“你感觉怎么样?”
“秋阳,你爹如果再不进食,可能熬不过今晚……”项观程面露忧色,“你爹这种情况是过度饥饿导致的,我们已经差不多3整天没有进食了,我还好一些,你爹以前整日劳作能量消耗比常人要快一些。”
“那……我该怎么办?”韩秋阳缓缓开口,“项前辈,你是否带了医刀?”
“带了,怎么……难道……”项观程倒吸一口凉气。
韩秋阳点点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现在理应还回去……”
他说完便接过医刀准备割下小腿肚上的肉给韩父喂下,他跪在父亲面前,“爹,孩儿无以回报,把血肉喂给你吧。”
“混帐!”韩父勉励睁开眼睛,气愤地破口大骂,“我已是将死之人,不需你此番相救,阿祥生死难料,家中只有你一个孩子,我希望你爱惜自己,好好活下去,为父年过七十,也算古来稀,死则死矣,你必须给我活下去,绝不可自残,如若你坚持割肉,我就在你面前咬舌自尽!”
韩父瘦弱的胸腔此起彼伏,他大口喘着粗气,怒目圆瞪地看着自己的儿子。
“爹爹……”韩秋阳放下医刀,泣不成声。
“项前辈,”一旁的杨荣忽然开口,“我曾经听说在大灾荒时代人们以血肉相食得以活命,所言不虚吧。”
“是啊,确实有这样的记载,秋阳为了救父亲也是如此做的……”
杨荣听闻沉思片刻,脸上露出一道奇怪的表情,他的眼角露出一丝凶光,嘴角微微翘起,“如果等人死后,再吃人肉,不算触犯刑法吧。”
空气瞬间凝重起来,周围没有人回应,韩秋阳的额头冒出微微汗水,他心里一惊,有了新的想法。
“你这是什么意思?”过了半晌,项观程开口打破了寂静。
“没什么。”杨荣轻描淡写地甩甩手,“晚辈就是随便问问。”
入夜,韩父似乎已经到了极限状态,他开始神志不清,嘴里喃喃自语,像是进入到某种梦境,生命岌岌可危。
韩秋阳拿起医刀冷不丁地走到杨荣身边,他用刀刃迅速地割开杨荣的喉管,杨荣的身体剧烈地扭动了几下,连眼睛都没有睁开,便在睡梦中死去了。他取来一只蓝色碗盆,把鲜血盛入其中,割下杨荣的鲜肉,一并喂给自己的父亲。
“这是……”韩父心头一惊,鲜红的血浆涓涓流入,他神情复杂,挣扎了几下便贪婪地吮吸起来。
随着血浆的滋润,韩父面部的黄蜡色渐渐退去,显示出一丝红润,整个人呼吸畅快了,精力也有所好转。
项观程眼见这一幕默不作声,随即脸上泛出一丝惊喜。
“秋阳,既然杨荣已死,老夫也吃一点吧。”项观程开口说道。
韩秋阳听了也盛了一些血肉给他送去,“前辈,晚辈也是迫不得已,如若不杀他,他便要吃我父亲的肉……”
“大道崩殂,也可理解,况且……老夫不会将此事说出去的。”项观程说。
“项前辈,如若我们能活着出去、我会去自首的,一人做事一人当。”韩秋阳淡淡说道。
“秋阳……”韩父叫唤着。
“爹,杀人偿命,我一定会去自首的,否则余生难安。”
韩父的眼眶湿润了,他轻声抽泣着,仿佛要把灵魂都哭出来消解掉。
“秋阳……”项观程看了看他,“既然如此,你也吃一点吧,至少先得活下去。”
“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吃人肉。”韩秋阳斩钉截铁地回绝。
数日时间里,韩秋阳只吃一些泥土和雪水,他刻意跟杨荣保持距离,也不再正眼凝视自己的父亲和项观程,剩余的时间里,他都闭着眼睛,尽量不让自己动起来,以此保存体力。
杨荣死后三天,暴风雪终于停止了,又过了一天,眼看着外面气温有些回调,三人这才松了一口气,扒开雪墙,从洞穴中走出来。
陈县令听闻陷入了沉思,过了许久他才睁开双眼,“此案本官判不了,小丁,小甲,你们去那个洞穴看看,先把相关证据收集起来,看看是否跟几人描述一致。”
“诺!”
“韩秋阳涉嫌杀人,本官依照律法必须把你押送大牢,等候宣判,本官念你一片孝心,本朝也着奉行以孝治天下,故而把案件陈述到州府,以求更为客观的审判,你可有话说。”陈县令盯着韩秋阳,目光坚定。
“草民,无话可说。”韩秋阳说。
衙役根据韩秋阳等人的陈述找到了杨炳和杨荣的尸体,经仵作验尸情况跟韩秋阳所诉吻合。据现场勘察,也没有发现与疑犯口供不符的证据。
陈县令面对洞穴案典册脸上露出一丝痛苦的表情,此案说复杂也简单,可如何审判似乎又不能一刀切,完全没有头绪。他找来师爷让他在案卷后面附上本府的意见,“本案面临诸多道德困境,本府不敢轻易下定论,本朝律令有明载:凡是谋杀人,并且造成已经杀害结果的,处以斩刑。此为本府律典建议,然律法中有自首免罪和留养其亲的相关律令,在本案中疑犯韩秋阳杀人并非出于恶意,乃是为了救父,事关人命、兹事体大,本府实不敢妄断,以免致有误判,影响社会公序良俗,此将本案走奏谳程序,还望江州府府衙准许。”
师爷一五一十记录下陈县令话语,并把案卷呈到他面前确认,陈县令看后点点头,派专人送往江州府。
江州府府尹大人王国藩审阅案卷之后同意了云阳县请求,他让人把案卷通过驿站送到京都,交由大司寇审理,以求圣裁。
大司寇王崇钊详细阅读案卷之后,随即召集了一批法律专家开始对此案进行分析。
“诸位,此案可有头绪?”王崇钊问道。
“此案确实令人不安,如若处以极刑,似乎也不妥当,此多事之秋,律法过重恐生民变。”右御史张庭云说。
“张大人所言有几分道理,但律法不清,恐难以服众,若是轻判,众人皆去模仿,世道可就更乱了。”左御史杨辉诺有所思地说。
“此案既然走奏谳程序,想来也是为了维稳,减少社会动荡,本案中杀人是事实,但似乎也情有可原,本朝律例中有免罪之例可循,本案却并不是适用,在案卷中云阳县提出‘自首免罪’和‘留养其亲’,根据《律》中记载,免罪之律只适用于没有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而本案中疑犯韩秋阳杀人属于重大事件,如果免其罪,有些不妥;至于留养其亲,《律》中规定只有家中独子且老人满七十五岁方才适用,疑犯韩秋阳固然已是家中独子,然其父韩千秋年满七十,不符合七十五岁这个条件,恐也难办。”
“这......”众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王大人,不知大人有何看法?”大理寺少卿刘少云问。
“诸位,老夫对本案有一些看法和意见,但也不敢妄自定夺,因此才将诸位召集起来,本案在法理上无话可说,却符合儒家伦理标准,自本朝太祖太宗立国以来,以儒道为尊,以孝悌治天下,我看案卷中提到疑犯韩秋阳本想把自己的血肉反哺给父亲,此乃孝子,然韩秋阳也并未躲避罪责,偶遇云阳县陈光县长,立即自首,丝毫没有拖泥带水,也不是作奸犯科之徒所能比也。”
王崇钊叹了一口气,继续说,“按照本朝律令,杀人者死,颠扑不破,人可以有私善,但国只能有一个公义,遵循律法办事,并未不妥。”
“王大人,”刘少云上前一步,“在下有一番见解,可否一言?”
王崇钊点点头。
“大人所言极是,本朝既然以尊儒道,不妨结合儒家经典,曾子曾言‘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尚书》也说:刑罚世轻世重。荀子言:治则刑重,乱则刑轻,本案中疑犯韩秋阳所为乃乱世之无奈,若是无有灾荒和风雪也不会发生这些事情,所作所为是迫不得已,而云阳县及江州府对灾荒赈灾不利,反而间接酿成憾事,如要判罪,则州府衙门也有罪。”
众人听闻,面面相觑,私下交头接耳,不知如何定论。
右御史张庭云沉思片刻后说:“诸位大人,此案关系重大,依本官之见,理应交由圣裁,古人云‘主者守文,大臣释滞,人主权断’,本案之情形理应交由人主亲断。”
王崇钊听了诸位专家的意见,脸上闪过一丝痛苦的表情,随后舒展开来,慢慢褪去,“既然如此,让书记官把诸位的意见写下来,明日待我面见圣上,交由圣上裁决。”
三日之后,一匹快马从京都出发,直奔云阳县。
半月之后,信使到了云阳县府衙,“云阳县令陈光何在!”他大声喊道,“圣旨到,出来接旨!”
陈光一听说有京都的使者前来传旨,赶忙穿戴好官府领着府衙全部人员恭恭敬敬地到大堂侯旨。
使者快步走到堂前,右手恭敬地托着黄色锦绣制作的圣旨,“此乃皇帝陛下圣旨,见旨如见真圣!”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人跪在地上对着圣旨行礼。
使者点点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云阳县韩秋阳一案,朕已知晓,韩秋阳杀人救父事件情有可原,然法理难容,朕思量多日,特下群臣大议,经由各专家所述,朕特下此诏,作为终审:依律当韩秋阳为谋杀已杀。死罪当诛,孝心可伤,其减斩刑,赐使自裁。钦此!”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人说道。
“陈大人,接旨吧,想必圣上说得够清楚了吧。”使者懒洋洋地说。
“臣领旨。”陈光颤巍巍接过圣旨,眼中闪着一丝泪光。
鹰溪涧下水流湍急,此处地势陡峭,四面峭壁,陈光带着两位衙役领着韩秋阳登上山顶,望着深渊,陈光表情凝重,暗黑色的涧底隐隐散发出一股寒气。
“韩秋阳。”陈光说,“无需本官多言了吧。”
韩秋阳走到峭壁边,从容自若,他一个纵身跳起来,在阳光下犹如一条泛着白光的青鱼,随着“扑通”一声,水面激起一朵浪花,须臾便消失在潺潺的流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