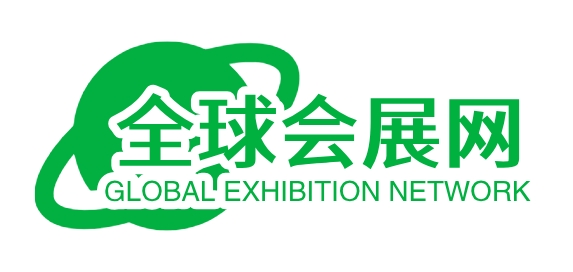二人并肩出了院落。
街上空空荡荡。
苟况低声说:“镇上的人都不见了,您……”
夫子说:“哪有不见,这不都在吗?”
话音刚落,忽然四周响起喧哗声,眼前亮起花灯如炬,一时人流穿梭,热闹非凡。
苟况说:“这……这是……”
夫子说:“纵横术罢了,一纵一横,是为时空,你从一开始就进了纵横术的迷阵了。”
二人说着,加快了脚步。
玉门客栈内,乐意正跪在王羽座下。
王羽说:“你跟了我这么久,学到了什么?”
乐意沉默。
王羽说:“你一身拳脚功夫都是白奇传授的。纵横剑术,你早就学会了,但那只是皮毛。这些年,你的纵横术一点长进都没有,你看看你身上的伤,有哪一种是不能化解的!跟了我这么久,到头来还是个莽夫!”
王羽轻捻胡须,说:“我很早就跟你讲过,你并不适合鬼谷,鬼谷要的是兵法、权谋、武力三者俱佳能继承鬼谷子之位的人。你呢?对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下完全不必要的重手,你是非得把在不合时宜的时候耀武扬威?不是夫子制止你,我也会出手。我已经把能教的都教给你了,你能领悟多少,全靠你自己的造化。”
王羽一声叹息,说:“回了西唐,你就自己乖乖回到白奇那里去吧。”
乐意说:“师傅,您不回西唐吗?”
王羽说:“我还有任务在身,不能带着你了,你自己走吧。”
乐意叩首拜别。
当他再抬起头时,王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翌日,乐意收拾妥当,策马西行。这是后话。
话说夫子与苟况离开后回到山庄,朱喜在门口迎接,那石碑已然换新。
苟况长舒一口气,说:“没想到世间竟有如此奇门异术,要不是夫子您及时赶到,我啊就危险了。”瞥了一眼石碑,“真要说起来,树大招风,名声太盛,反而招致麻烦。”
夫子笑道:“你我本就是要兼济天下之人,福祸总是难免。况且,这石碑,我是故意留在这儿的。”
朱喜说:“夫子何意,弟子不明,请指教。”
夫子含笑,敲打苟况的肩头,说:“你看看你这个学生,好学好问好思,就是不通人道。我留下这块碑,就是为了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值此天下变局,哪能坐等战事上门。”
夫子说笑一番,飘然而去。
待夫子走后,朱喜问苟况说“夫子,适才夫子敲打了您肩头三下,这是何意?”
苟况笑出声,说:“你想太多了,你应该多去山下走走,而不是整日待在书院里。”
忽然,苟况正色说:“那个闯山门的青年,我今日与之交手,你猜怎么着?”
朱喜说:“那人尚且年轻,功力定然不及夫子十之一二,夫子何须一问。”
苟况摇摇头,说:“再猜。或者我问的更清楚些,你猜胜负几何?”
朱喜一惊,说:“此人竟能胜了夫子几招?也着实是难得。”
苟况说:“是我输了。”
朱喜愣住。
苟况说:“若不是夫子赶到,我已深受重创。”
朱喜说:“鬼谷一派竟真有如此本领。”
苟况说:“我素来不喜习武,拳脚功夫更是疏忽,连带得你们也步我后尘。但生逢乱世,圣贤山庄要想有所抱负,非得崇武不可。如今圣贤山庄,可谓青黄不接,夫子与姜夫子都是当世高手,我这儿就开始掉凳,到你们这一代,人人都读成了书呆子,以后圣贤山庄在天下如何自处还是个问题。”
朱喜说:“弟子谨记教诲。”
苟况摇头苦笑,说:“你啊,就不是那舍得动自己手的人,再看吧。对了,没有惊扰到姜夫子吧。”
朱喜面色刷地凝重,说:“您离开前叫我准备好后手,我便去了三省崖,本想知会姜夫子一声,但姜夫子他不在三省崖。”
苟况一怔,说:“竟有此事?怎么没派人找?”
朱喜说:“夫子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