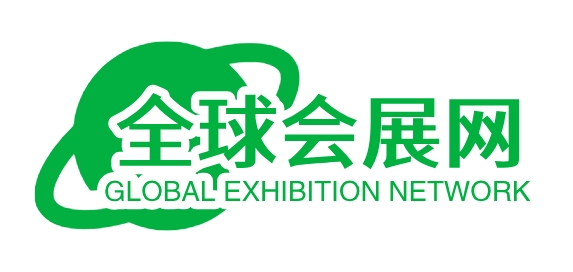她想笑。看到笑话想笑,听到有趣的事想笑,困惑时想笑,尴尬时想笑,遇到好友想笑,面对阳光想笑。就好像是被触发了一个开关,她可以恢复着对着人笑了。
这是一个历史性转折。还记得那年,她躲在办公室里,害怕得发抖,日子一天一天数着过,她什么都不指望,只盼着出了结果后是无事发生,只要无事,她便可以舒一口气了。
经年累月的创伤让她长期处在焦虑和抑郁的情绪中。去年的那个时候,她一个人坐在便利店,啃着微波炉加热过的预制包子,心里像是被一阵阵抓着难受,店里恰好在放周杰伦和五月天的音乐,她打电话给远方的朋友,电话接通后,她也没说出怎么个事情来,眼泪止不住地流,反反复复地说着自己压力好大、好累。事实上,现在的她早已忘记当年的处境了,但唯一还无法忘怀的,是痊愈过后被压在记事簿中的仇恨。
在这个世界上,与仇恨相关的天命,有好几种,而她一人就占了一种。光滑的皮肤白皙透亮,涂上凡士林后,皲裂的细纹处奇痒无比,静静忍受此种非典型痛感,终于有一天伤口愈合,时间治愈了一个似乎从未存在过的伤口。她曾放过这句话——向我扎刀子的人儿,不会有一个好了的。事实上,她从没做什么,只是涂几层凡士林罢了,这无为的天命就这么成了。
在这些个短暂又漫长的日子里,沉默与愤怒角斗、感受与回忆角斗,她与她的外壳角斗,她始终是陌生的自己,没有主人公出现在故事里,稀薄回忆并无具象,直到被人拉着拽出这条暗沟,惊恐才得以停止。
没有谁能走出你的仇恨,她的伤口只涂凡士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