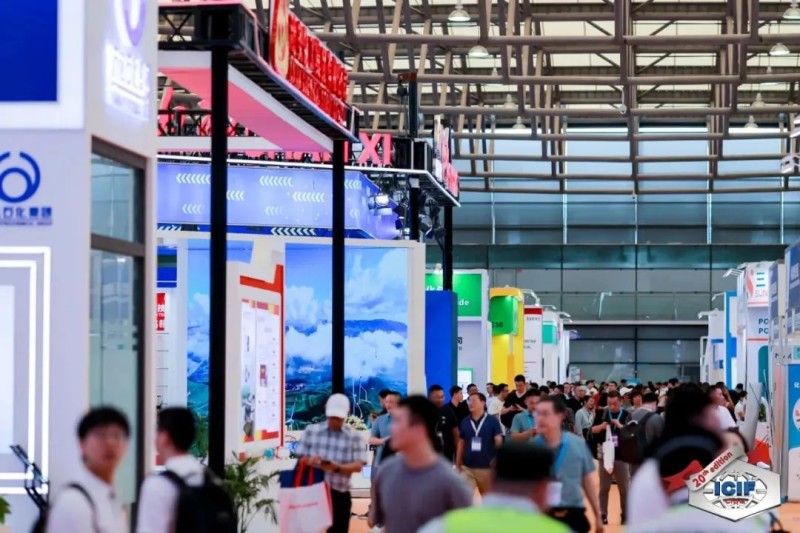窗外,城市的霓虹渐次黯淡,只剩几盏孤灯,在角落里散发着清冷的光晕。马路上偶尔驰过的车辆,划破寂静,转瞬又将寂静缝合。
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思绪像脱缰的野马,肆意狂奔。白日里那些未竟之事、说错的话,还有缥缈的未来憧憬,都在这黑暗里无限放大,纠缠成解不开的乱麻。
月光如水,透过窗帘缝隙,悄然洒在床头,似想慰藉却又添几分落寞。身旁的闹钟滴答滴答,每一声都敲在空落的心间,时间被拉得漫长又煎熬。我抱紧被子,妄图捕捉一丝睡意,可清醒却如附骨之疽,甩也甩不掉。这漫漫长夜啊,成了我独自徘徊的荒芜之境。
窗外,城市的霓虹渐次黯淡,只剩几盏孤灯,在角落里散发着清冷的光晕。马路上偶尔驰过的车辆,划破寂静,转瞬又将寂静缝合。
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思绪像脱缰的野马,肆意狂奔。白日里那些未竟之事、说错的话,还有缥缈的未来憧憬,都在这黑暗里无限放大,纠缠成解不开的乱麻。
月光如水,透过窗帘缝隙,悄然洒在床头,似想慰藉却又添几分落寞。身旁的闹钟滴答滴答,每一声都敲在空落的心间,时间被拉得漫长又煎熬。我抱紧被子,妄图捕捉一丝睡意,可清醒却如附骨之疽,甩也甩不掉。这漫漫长夜啊,成了我独自徘徊的荒芜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