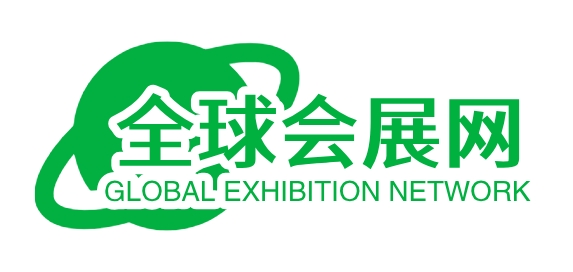中华契约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数千年中华民族绵延发展中社会秩序构建和体系制度维护的重要基础。契约合同是传统文献史料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各种考古发现和存世的文献史料中占有很大比重。长期以来,学界对契约材料开展多方面研究,尤其在契约及其内容、格式的历史演进方面,成绩卓著。然而,对于契约文化及契约精神本身的综合性研究则相对欠缺,乃至诸如“中国人缺少契约精神”“中国商事契约起源甚晚”等严重失实的结论盛行,实属对中华传统法律及契约文化的误读。
中华契约文明的源起及演化
契约是什么?从表象看,它是一件件个人之间通过签字画押,或许同时还是经多人见证的约定。就形式而言,如果只是从近现代的社会实践来看,所谓“契约”,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以纸质书面形式存在的缔约约定。然而,如果我们拉长历史的视界,则会看到,从古至今,其可能采用书面、口头或者其他各种特殊的记录或形式(仪式),比如结绳、刻石、刻木,乃至歃血为盟、烧香许愿、祭拜烧纸等。这种约定最重要的是其背后深刻的社会秩序意义,更进一步则是追究到其效用及实现机制。契约合同,包括后来在此基础上演化出来的种类、形式多样的票据、文约、各种文书等,其本质是各种特定社会关系的构建与维护,其实际的目标指向则在于秩序。
中国古代立约行为起源甚早。上古(原始时代末期)先民结绳而治,一般名之曰“结绳记事”或“结绳计数”,通常被视为古代数学计算和会计、统计等的起源。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结绳之法,在古人的理解中,并非只是记录或计算,而是具有后世“书契”缔约之意。也即是说,上古先民用结绳之法,在计算、记录的同时达成缔约之目的,从而施行对官私各种行为的治理。后世圣贤在文字发明的基础上,以“书契”代结绳,行治理之实。“听取予以书契”,即是以书契作为判别各种收付(支)合法性的凭据。王旭《契纸千年:中国传统契约的形式与演变》中曾详细分析中国古代契约的早期起源,认为:“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最早的契约包括:‘质剂’、‘傅别’和‘书契’,它们分别适用于不同类型的交易,即‘听称债以傅别’、‘听取予以书契’、‘听买卖以质剂’,也就是说它们分别适用于买卖、借贷和收受赠与。” 质剂、傅别、书契的这种形式区别,充分考虑了商业交易(买卖)、借贷、收受赠与的业务特点,也影响到后世契约形式的发展。
竹木简牍作为纸张普及之前最重要的记录载体,在其长达千年的使用中,在契约形式的发展方面曾有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考古发现的汉代契约文书多采用竹木简牍形式。其以“券”为名,体现出如同质剂、傅别、书契的形式区别。大约自公元7世纪中期以后,民间普遍采用“立契”方式来规范各种关系(包括经济关系)和行为(如租赁、借贷、买卖、典当等),并常用“恐人无信,故立私契”“官有政法,民从私契”“恐后无凭,故立此契”等用语来说明契约的意义。这种习惯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明代中晚期商业的发展和日用类书的刊行,为契约形式的多样化、类型化和普及提供了极大便利。合同的形式与意义至清乾嘉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清人翟灏在其所著《通俗编》中,就曾提到当时人们使用合同文契的情况:“今人产业买卖,多于契背上作一手大字,而于字中央破之,谓之合同文契。商贾交易,则直言合同而不言契。其制度称谓,由来俱甚古矣。”
当代合同与传统契约的不同
当代合同实质上可视为“大陆法系契约”,其与中国传统契约之间有着明显差异:一是契约的分类标准,中国传统契约的分类采用二元性分类标准,既包括交易行为类型又包括交易对象的考虑,而大陆法系契约分类的标准总体上看是一元性的,即交易行为类型。二是关于契约本体论的讨论是传统契约与当代合同(或大陆法系契约)之间的另一个巨大差异。尽管在吐鲁番契中有“二主先和后券”“三主和同立券”,甚至于“九主和同立券”,在敦煌契约中也有“二主对面平章”等用语,表现了传统契约“合意”的行为,但是该处“和同”所表现的“合意”状态,不能简单地直接认为是当代合同的“意思表示一致”。宋元之后,这种表述又被“三面评议”“三面言定”等用语所取代,因此相对于当代合同(或大陆法系契约)形成的“合意”本体论,或者“意思自治”的核心说,不可能相提并论。三是传统契约也没有当代合同(或大陆法系契约)那种成熟的法律规范性。尽管在中国历史上比如南宋时期曾经有过官颁契纸,但是像当代合同(或大陆法系契约)那样,以系统的契约法律规范契约行为的情况,在中国传统社会史中没有出现过。
因此,当代合同的情况,与近百年来其他领域的情况相类似,不论是形式还是理念、内含思想方面,很大程度上都受到西方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西方制度、文化的移植。其与中国传统契约存在很大差别。除了上述各方面外,最根本的是两种文化之间本源上的差异。概而言之,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的差异。当代合同是西方制度文化所代表的工业化下标准化生产的产业(工业)制作,而中国传统契约尽管也受范本以及日用类书所提供的格式化标本的影响,但现实中的每一件文书,几乎都是带有个性色彩的个性化创造。其大体格式有所“规定”(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民间习惯),但具体的意思表达、文字使用和内容的阐述,却是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这是由中华文化重意不重形,注重内涵和理念表达的文化特点所决定的,也是中国传统契约最大的特色。
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文化(包括西方法律和契约文化)的进入,逐渐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导致传统契约文化日渐式微乃至最终全面退出历史舞台,大陆法系契约成为主流,引入了不同的合同观念。这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了与传统的割裂,造成今天我们在理解和研究古代契约原始材料和相关文化时产生困难。
总之,中国传统契约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上古结绳记事到《周礼》六约,就已经深刻奠定了契约的广大而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体现出深刻而坚韧的社会秩序价值。天人合一、万物并生、和谐与共,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也是中国契约文化的根基所在。中华传统契约文化所承载的精神理念,可以助力构建一个共同发展、互惠互利、和谐有序的人类生存和生活环境,这是中华文明奉献给全人类的宝贵文明财富。
作者系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文博中心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程纪豪
新媒体编辑:曾煜婷
如需交流可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