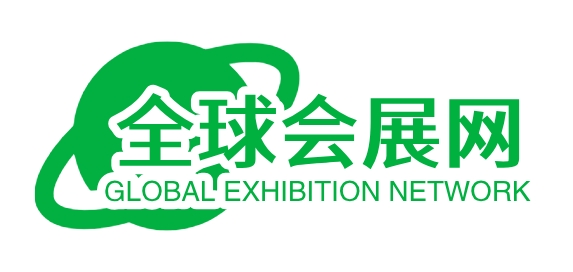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秦腔的。只隐约记得大约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村里大人一忽悠,我就会像模像样地开始唱,还带着动作,大人们就在一旁笑呵呵地围着看。至于唱的什么,现在已完全没有了印象。我想,一个四五岁的孩子,能唱些什么呢,不过对于秦腔的喜爱应该是从比这更小的时候开始的吧。
秦腔是流传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一带的一种地方戏。在这些地方,人们对秦腔的喜爱到了什么程度,有一句话概括得非常形象,“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齐吼秦腔”。你也许认为这有些夸张,不过对于喜爱秦腔的人们来说,我看一点都不为过。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只要那里唱大戏,人们就会从四面八方聚拢来,有的甚至从四五里外的地方赶来,就是为了听那些熟悉的旋律,看那些演员的做派、打扮,套用现在流行的一句广告语——就是这个味!引申了说,就是喜欢这个味。
记得那时候,三村五社就会有一座戏楼。戏楼大多是周围的村子共同出钱建的,也有原来的庙宇,破除迷信时被改造成了戏楼,老家那里的戏楼就是这样,其余的庙房就改成了学校,办的是初中,周边村里的孩子上初中都到到这里来。戏楼是由大殿改造而来,就在整个学校的中心。记得每年二月二龙抬头,这里就会举办庙会,唱大戏当然是庙会的主要活动之一了。一方面开春了,人们需要买些生产物资,以备农忙时用,另一方面,就是用唱大戏这种传统来祈求新年里五谷丰登、生活幸福。
一大早,周边村里的人们开始陆陆续续地集拢来,你会编笼,我会做叉,你有没吃完的红薯,我有存下的老南瓜,他炸的油糕远近闻名,她拌的饸络闻了就让人口水顿生,我家需要个收麦的镰刀,他家缺个扬场的木锨......于是大家就借着庙宇前面的公路和学校的操场,买的卖的,吆喝着,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讨价还价。孩子们更关心的是好吃的,家里给上五毛钱,买上一个酥得掉渣、咬一口烫嘴巴、甜得直到嗓子眼的油糕,吃一碗油漉漉、软活活的、辣丝丝的凉拌饸络,然后爬到戏楼上,和着一群孩子上下地闹腾,布置戏台的师傅实在烦了就骂上几声,把他们轰下来。各种家伙什儿一摆好,演员们也都化妆好了,穿戴整齐在后台等着了。这时候大幕就会拉上,锣鼓家伙就会一齐敲响,这是在叫人呢。听到锣鼓声,人们就迅速地聚过来,密密麻麻的人群站满了戏台前的小广场,就连树上都有人。大幕徐徐拉开,演员们忘我地表演,观众们痴痴地看,看到精彩处,掌声骤然响起来,台上的演员更卖力地演;看到伤心处,台上的演员哭腔悠长,台下的观众眼中闪着泪光,有的眼泪流到了嘴角,也不顾去擦。此时台上台下仿佛融为一体,演员在情境里,观众也在情境里。及至散场,人们仿佛还没有从戏里出来,只顾走着,也不说话,过上一阵子,才有人慢慢回过神来,评论一下演员,交流一下剧情,人们这才七嘴八舌地说开了,脸上也有了笑容。那是一种过罢隐后非常满足的笑容。
戏匣子的出现,让戏楼渐渐冷清了下来,有的慢慢闲置、失修,最后拆的拆了,挪作他用的挪用了。戏匣子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收音机,之所以叫戏匣子,大概就是这玩意儿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用来听戏而来的吧。其实,在今天已经几乎快要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的戏匣子,在当时并不是家家户户都买得起的,只有那些家境稍微宽裕一点的人家才能享受得了。只要谁家买了一个戏匣子,村里人就会你传我我传你地传开了。有了这稀罕物件的人家也不藏着掖着,总是喜欢拿出来显摆。主人抱着戏匣子,把声音开得大大的,踱着方步,在村中间的小路上悠哉悠哉地走着,一群孩子好奇地跟着看稀奇。大人们大多好面子,不会马上围拢来,有实在忍不住的,就会装着顺路,靠近了搭讪,问这问那。人们实在搞不懂,这么小一个匣子,怎么能装那么多人,还有那些家伙什儿,怎么摆啊!主人就会鄙视地看那人一眼,不懂装懂地说一些那人听也听不懂的话。那人实在好奇,伸手想摸摸,主人马上一脸的严肃,把戏匣子抱的紧紧的,生怕那人给弄坏了。只要戏匣子里一开始放秦腔,那些大人们也就忍不住了,三三两两地围拢来,人多了,主人家就把戏匣子小心翼翼往地上一放,大家众星捧月般围在周围,席地而坐,如醉如痴地听着,听到熟悉的,也跟着哼几句。他们不光听,还要交流,为此还常常争论不朽,弄得脸红脖子粗。人们后来才弄明白了,其实戏匣子里并没有人,声音是从很远的省城那地方,通过一种什么波传过来的。于是,有一台能唱戏的戏匣子就成了人们的渴望。
那时候嫁女,最起码的要求就是三转一响。这三转就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一响可就是被人们称作戏匣子的收音机,后来就演变成了收录两用机。这些东西当然是由男方提供的。快要结婚前,男方带着女方就会去置办齐这些物件,到了结婚那天,新娘子戴着男方给买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戏匣子则由男方的迎亲的人推着、抬着,和着女方家的陪嫁,浩浩荡荡地送到男方家里。这戏匣子摆在最前面的花架子(用于抬陪嫁品的一种工具,主要放一些小物件,如做的布鞋、绣的门帘、镜子、木梳匣子等)里。
迎亲的队伍每经过一处村庄,就会被看到的人喊着停下来歇歇。其实不是真的想着抬的人走累了让他们歇会儿,而是想看看这些嫁妆。大姑娘看的主要是那些鞋底和鞋垫,遇到自己喜欢的样式就多看会儿,暗暗记在心里,回去照着纳;小媳妇看了,就会想起当年自己的陪嫁,暗自比较着;家里有待嫁的女儿的老妈妈看了,就会在心里盘算着,该给女儿准备些啥。迎亲的队伍到了自家的村头,男方家早就派人等在那里的,马上就会燃放起鞭炮,于是村里的大人小孩都会跑出来看,这时候抬嫁妆的人就会停下来,把花架子、箱子一溜儿摆在村口的大路上,摆在最前面的花架子里的戏匣子还在热热闹闹地放着秦腔,在热闹的秦腔声中,人们笑着、看着,不时地和身边的人说上几句赞美的话。戏匣子上闪着七彩的光。
那时候的戏匣子在乡亲们的面朝黄土北朝天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农忙时,你会发现,在忙碌着的人们不远处的,戏匣子摆放在田埂上,用高昂的秦腔,为忙碌的人们驱赶着疲乏。农闲时,人们三五成群沿墙根蹲着,戏匣子就放在面前,及到吃午饭的时间,人们也不愿散去。家里已经做好了饭,妈妈就让孩子去喊大(陕西习惯把父亲喊大)回来吃饭。孩子寻了板胡的声音找过来,“大,我妈叫你回去吃饭呢”。戏正听到关键处,那个愿意离开,大人就冲着孩子说,“去,给大端来。”孩子老大不情愿地转身,一会儿就端来一老碗臊子面,吃着臊子面,听着秦腔,简直是嘹咋咧(陕西方言,很美的意思)。我想,这也许就是陕西人吃饭为什么喜欢蹲在大门外和用老碗的缘故吧。有时大人还要嘟囔一句,说是这面里头辣子放少了。
戏匣子满足了乡亲们对听戏的渴望,可总有些遗憾,就是无法看到演员。秦腔不光是听音,有很多还是要看表演,如闪帽翅、甩水袖,耍花枪、还有喷火等等,有的根本就没有唱段,看的就是演员的耍绝活。电视机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这一点。刚开始出现的电视机是黑白的,记得村上第一台电视机是老村长在城里工作的女儿孝敬老人家给买的。这一下,老村长家成了乡亲们晚上的活动站。等到晚上喝过汤(老家管吃晚饭叫喝汤),人们就不约而同地来到老村长家看稀奇。老村长也不嫌弃,客客气气地让来人随便找个地方坐了,板凳不够的就坐炕上,炕上坐不下了就找个地方站着,每次都要看到很晚。后来黑白电视机慢慢多了起来,老村长家也就没有那么热闹了。可毕竟这黑白电视机和人们平时看到的有差别,就是色彩太单一了。后来听说邻村有个让黑白便彩色的法儿,大家就都跑去看。那人家见人来的多了,就把电视机搬到大门外边,人们就站在场(陕西管门前较大的空地叫场,主要用于农忙时碾打晾晒)上看。其实也并非正真的彩色电视机,只是表面蒙了一层彩色的塑料薄膜,薄膜上有三种颜色,上面三分之一是蓝色,中间三分之一是红色,下面三分之一是绿色。虽然如此,人们还是在遇到电视里放大戏的日子跑来看,有颜色总比没有颜色好。
记得村上第一台正真的彩色电视机是老爸从城里买回来的旧货,只有十六寸,花了六百多块,老妈虽然喜欢,可一听六百多块,脸色顿时就非常难看,说老爸胡成精。等到了晚上,村民们都跑来看,由于家里太小,老爸就把电视机搬到外边。天线就架在房顶上,老爸喊我上了房,把天线来回地转,老爸在下面调频道,直到老爸喊一声好了,这才固定了天线。平时的人要少些,就在屋了看了,等到唱大戏,来的人就多了,只有搬在屋外了。后来彩色电视机普及了,姑娘陪嫁的三转一响中的一响也变成了电视机,家家户户就在自己家里看了,这都是八十年代后期的事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对秦腔的喜爱更多的是来自父母亲对秦腔的喜爱。无论在和他们一起干完活回来的路上,还是在家里,他们嘴里哼的大多是秦腔。戏匣子平时不开,一开放的准是秦腔。到后来电视机里,一到放秦腔乱弹,那是非看不可的。也正是这样,我们对秦腔的喜爱越来越深。慢慢地我知道了很多名家,李爱琴、任哲中、李正敏、肖若兰等等等等,而且还记住了很多折子戏。有时候听到熟悉的段子大人们一下子想不起来是谁唱的,我就能一口报上来。很多唱段,我模仿的非常像,村里人都说就像原唱一样。有些人就鼓动我妈让我去学戏,妈妈也还真心动了。记得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妈妈就带我去考过一次戏校。那时候太小,考试的时候让我唱一段,一紧张,竟然唱了“一颗螺丝帽”,考官直接就让我出去了。等到上了初中,有戏班子来招生,我也去考了,就连原来在戏台子上唱过的自乐班的人也都来考试了,可惜还是没有能考上。后来也就不去想进戏班子了,就想能进戏院正真地看唱戏。记得每年正月十五离我们十多里路外的县城里都要刷社火,有时也会请城里的正规班子来唱戏,这可不是免费让看的,要门票,其实票价也就是三五块,可家里人从来舍不得去看,更别说带我去了。后来有一回,妈妈一狠心,就带我去看戏了,记得那是唱的是《铡美案》全本,第一次现场感受专业演员的表演,那个过瘾啊,直到现在我还不能忘记。
后来我上学离开了陕西,秦腔离我越来越远。再后来在外地工作了,再也没有看过一场秦腔。其实秦腔不光是离我越来越远,就连现在的陕西年轻人,不要说能唱了,就连喜爱者也已经寥寥无几了。听家里人说,自乐班几乎已经全部散了,只有正规的一些单位,还承载着研究和传承秦腔的重担,可那深深烙在我骨子里的秦腔,还不时在耳旁回响。借助着互联网,我们才能把以前的一些熟悉的段子听上一遍。自己有时也哼上一段,心里有说不清的滋味涌现。那曾经教会我爱与恨、美与丑,并培养了我文学萌芽的秦腔,还有我那些喜爱秦腔的老乡,如今也只能在回忆中,才能体会、玩味了。
吼一声秦腔,神清气爽;吼一声秦腔,热泪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