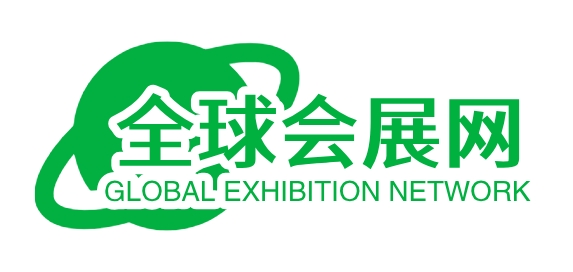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小编暖心提醒,音乐相伴更有感觉~
李兴艳
自己像个“坏掉的容器”
深夜,城市渐渐沉睡。河北省“12356”心理援助热线中心内响起铃声。电话接入,话筒那端传来的并非如惯常那般的哭诉或是爆发的情绪,而是一种更深的、几乎令人窒息的沉寂。过了许久,一个极力压抑却还是透出极度疲惫的女声响起:“你好……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觉得心里堵着一块巨大的石头,很沉,很难受,很多年了。”这位自称小杨的30岁女性,声音里充满了无处可逃的痛苦。
在30岁的年纪,人生本该绽放,但小杨的世界却被一层无形的厚茧包裹。她描述着一种难以名状却深入骨髓的沉重感,就像背负着一座无形的山,疲惫不堪却又无法卸下。睡眠成了奢侈,即使入睡也常被模糊却令人心悸的梦境惊醒;明明心里难受得像要炸开,眼睛却干涩得像沙漠,一滴泪都流不出来。这种情感的割裂,让她觉得自己像个“坏掉的容器”,既无法盛放悲伤,也无法将其倾泻。
刚开始通话时,小杨除了不断哽咽和短暂沉默,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表达,话语零碎而克制。热线咨询员并未急于追问,而是用稳定的语气一遍遍回应:“没关系,你可以按自己的节奏来,我在这里陪着你。”一段时间后,咨询员轻声问出一句:“你还好吗?”这句话仿佛轻轻触碰到了小杨内心深处的柔软角落,她突然抽泣起来,并艰难地组织语言。那段尘封的记忆,终于一点一点地浮现出来……
你会对7岁的自己说什么?
原来,在小杨7岁那年,母亲因病骤然离世。年幼的她,尚未来得及理解死亡的重量,就被匆忙推入一个被迫“坚强懂事”的角色里。大人们忙于处理丧事,只是反复叮嘱她:“别哭了,你要坚强!”懵懂的她,将这份巨大的悲伤和对“乖孩子”的期许一起,深深压进了心底的角落。
多年来,她努力学习、工作,努力扮演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仿佛那段失去母亲的童年从未存在。然而,这份未曾充分哀悼的伤痛,如同一个被遗忘的“时间胶囊”,在30年后,以弥漫性的痛苦、情感的麻木和身体的疲惫,悄然释放出毒性。
听了小杨的故事,咨询员温柔而坚定地回应:“7岁那年,那个小小的你,突然失去了最依赖的妈妈。那时的你一定很害怕、很无助、很舍不得,心里有很多话想对妈妈说,也有很多眼泪想流,对吗?那个小小的你,当时一定需要一个拥抱,需要一个允许她放声大哭的地方吧。”
刹那间,电话那头长久维持的、仿佛坚不可摧的情绪壁垒出现了一道细微的裂痕,小杨的声音有了一些颤抖。咨询员敏锐地捕捉到这丝变化,继续轻声引导:“小杨,如果此刻,那个7岁的小女孩就站在你面前,你会对她说什么?她那么小,那么害怕,她需要你的看见,需要你的允许……”
这句话终于击中了小杨内心最脆弱的核心,长久以来被理性牢牢锁住的情绪闸门轰然洞开,一声压抑到极致的、仿佛从灵魂最深处撕扯出来的呜咽骤然响起,积攒了二十多年的委屈、恐惧、不舍和思念让小杨泣不成声。咨询员没有打断,只是稳稳托住这份迟到了许久的巨大的悲伤,用温和的呼吸声和简单有力的话语给予陪伴。
这场酣畅淋漓的痛哭持续了很久。当汹涌的浪潮逐渐退去,小杨的呼吸变得深长而平稳。她虽然带着浓重的鼻音,声音却透出久违的清澈:“老师……我感觉心里那块堵了快一辈子的石头……好像松动了……虽然还是很累,但轻快多了……”
完成一次迟到的告别
小杨的故事并非孤例,它是无数“未完成哀悼”者的缩影。当生活出现重大变故,个体因年龄、环境、社会期许等原因未能充分体验和表达哀伤,这份未被处理的情感并不会消失,只会被压抑。它可能化身慢性的抑郁、莫名的焦虑、身体的病痛、情感的疏离,在多年甚至几十年后,以更隐蔽也更顽固的方式侵扰生活。
心理援助热线的核心价值,正是提供这样一个安全、即时的容器。在这里,没有评判,只有接纳;没有催促,只有陪伴。专业的热线咨询师能运用共情、倾听、情绪正常化等心理支持技术识别那些被时间掩埋的伤口,用共情和理解,引导个体穿越时光,去拥抱和安抚当年那个受过伤的孩子,为更深层的心理修复打开一扇窗。
但这里需要提醒并注意的是,拨打援助热线意味着期待温暖的倾听和专业的建议,但它不能替代长期的陪伴和系统的治疗。心理援助热线更侧重于提供紧急情绪支持与初步心理疏导,而真正的疗愈之路,还需在现实生活中稳步开展。不过,在热线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时间仁慈地允许我们回头,去拥抱那些被遗落在岁月深处的悲伤,完成一场迟到却至关重要的自我和解。

文: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李兴艳
编辑:魏婉笛 马杨
校对:杨真宇
审核:李诗尧 徐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