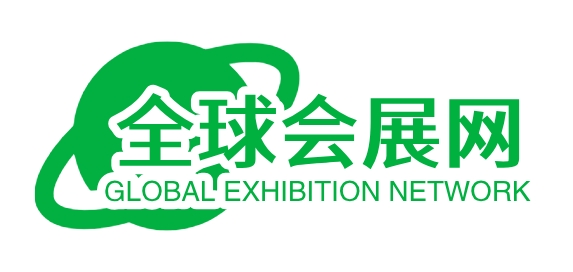“在案子没有处理完时,心里像是有一块石头压着。(调解)当天,也没觉得这条路怎么样。在看了现场基本情况后,给双方做思想工作,差不多调了一个早上。也是像今天这样的大雨,坐在田棚里面调解。”7月22日下午,法官前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梯田深处,就一起涉梯田相邻用水纠纷调解案件进行回访,记者随行采访。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对法官来说“没啥”的一条路,却让记者一行汗如雨注。踩着碎石泥巴路,一脚深一脚浅的,管得住腿管不住脚底,稍不注意就会踩到热乎新鲜的原生态粪肥。
“这也算是(路况)好的了,之前还有个梯田纠纷案,像这样的小路都没有,法院去的每一个人都摔到田里了……”听完法官一席话,一行人继续埋头“行路难”。
穿过丛林已耗费大半体力,入眼一大片翡翠绿,刺眼的阳光来不及躲避,还带来紫外线灼烧的微痛感。
“现在的背对背,是为了将来还能面对面”
这一类涉梯田纠纷很是常见,“敢破坏我的田,就不让你家牛通行”。原、被告两家承包的梯田相邻,被告在上方,原告在下方。此前,被告家的牲口经过原告家水田,时常会践踏农作物,为此,原告架起围栏不准牲口通行。而后,被告将自家水田出水口改道,使得原告家水田无法正常灌溉,改种玉米地。双方争执时有发生。

图为案件回访现场。
抵达纠纷现场后,原本晴朗柔和的天空,风云变幻间,凝聚起厚厚的积雨云,大雨侵袭从不提前打报告。法官微微一笑道,这在雨季的云南是家常便饭。
吴仙,云南省元阳县人民法院法官,土生土长的哈尼人,擅长用哈尼语跟涉梯田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作沟通。即使办案多年,她面对当事人也依旧带着大姑娘般的腼腆微笑,有一回甚至连当事人都没有认出她就是办案法官。
同样的大雨,同一片梯田,将吴仙的思绪拉回调解当天。“我记得调解当天,有一方本来是要走了,说要回去干农活了,不想再调解了。我就跟他说,下这么大的雨,哪里也去不了,不如就在田棚里面聊聊天噶……”

法官对案件进行现场调解的田棚(元阳法院供图)。
一场调解,在瓢泼大雨的梯田田棚里进行着,骤雨时下时停,仿佛也带着情绪在叫嚣着要发泄。一调就是三四个小时,在家长里短和释法说理中,大雨浇灭了当事人的对立情绪。
吴仙说,其实涉梯田纠纷处理的都是邻里关系,年轻一辈子女都不在场,守田老一辈闹矛盾的居多。有时候因为你骂一句我怼一句,往往就是嘴边多说了那么一句话,情绪上头了,互不退步没法调解。
记者:那当时您说了什么,最终触动了他们呢?
吴仙:“邻里之间没必要闹这么大的矛盾……两家的梯田世世代代都在这里,你自己也背不走,你的后代也背不走。后人在地里干活,还不是要面对面,有时候还需要对方帮忙。”
哈尼人自古就是勤劳的农耕民族,他家谷子需要收了你家去帮忙,你家玉米亟待撇了他家来帮忙,团结互助是梯田农耕千年历史铸就的村规民约。
借用一句话:“现在的背对背,是为了将来还能脸对脸。”
对哈尼人来说,梯田就是命根子。为了梯田和后代考虑,双方最终各退一步,达成调解。原告当场就把自己架在双方梯田之间的围栏拆除了,被告也同意日后不牵大牛以免踩踏原告玉米地。
“事情处理完回去的时候,我才感觉到脚下的路原来这么难走……”来时心压大石块,不觉脚下行路难,吴仙笑着回忆道,那天纠纷调解结束时,也刚好雨过天晴。法官的情绪也随之再次灿烂。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一辈子伺候这个水田,干得动就一直干”
“从近几年昆明环资法庭的受案情况来看,主要还是取水权纠纷占比较多,大约占60%,其次是排除妨害纠纷,比如双方当事人在田埂中修建挡墙引发的纠纷,此类案由大约占20%,其他比如相邻纠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等占20%。”昆明环境资源法庭法官助理曾佳提供了一组涉梯田纠纷案整体数据。
背依梯田这座“幸福靠山”,靠天吃饭的农耕民族,讲究一个天时地利人和。每年3、4月枯水期,正逢梯田大量用水的插秧时节,也是涉梯田用水矛盾最多的时候。
“‘合’字下面有个‘口’,人与人之间闹了矛盾要用嘴来讲和,‘拉’字有个提手旁,握手言和的意思。”元阳县新街镇全福庄村委会党总支书记卢卫明,也是“合拉调解室”主理人介绍道,合拉调解室日常主要调解山林水土类纠纷,每年大概有2、3件涉梯田纠纷需要调解。“合拉”两个字在哈尼语中意味“好呢、满意”。
据卢卫明回忆,2024年发生一起比较典型的涉梯田取水权纠纷,两家梯田之间有一汪“龙潭水”(即山泉水,当地说法),一方想迁引龙潭水到自家梯田里,但泉水出在自家梯田里的村民却不同意,双方起了争执闹到合拉调解室。

拍摄于元阳梯田某处山泉水。
“我们在现场勘察完后,就请他们到合拉调解室坐坐,讲明水资源都是国家的,不是个人的,(龙潭水)大家可以共用。先满足出泉水一方的三亩梯田用水后,再满足另一户需要用水的村民。”双方接受了调解,也都表达了满意。
梯田是命根子,水是命脉。“一辈子伺候这个水田,干得动就一直干”,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就算一年下来挣得不多,梯田也是割舍不下的根,尤其老一辈哈尼人对梯田的感情更深。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村民正在清理梯田杂草。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是因为天气不好,街上看不到村民。而是哈尼人还在你睡觉的时候,就一大早把地里农活干完了。”
涉梯田事宜不论大小,分毫必争。据了解,村村寨寨每户人家大概能分得3、4亩梯田,“一亩田虽挣不了多少钱,但却是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也要完完整整传承给下一代。”这是哈尼人一辈子的执着。
既然哈尼人有共同的追求和目标,那当矛盾发生时,自古习得的村规民约就成为了解纷的切入口。在法院引导下,村委会整合多方资源,内部直接将矛盾消融,大事小事不出村寨。

村民正在巡视梯田状况。
当问及全福庄村成为“无讼村”后有何深刻改变时,卢卫明表示,自从在合拉调解室搭建了共享法庭,附近村寨也能共享司法资源,惠及一方百姓。法院会引导合法合规地进行调解,兼顾情理法,应重要农事节点入户宣讲普法,答疑一方村民。对乡亲们来说,“不再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才是真实的’,村寨乡亲们整体法律觉悟也有所提升。”
“哈尼人家的梯田会呼吸,是活着的,生长的”
“俩家族都有来,当时双方讲话都冲,为争一口气,情绪一时激愤,调解有难度……怕矛盾再次激化,也一直没敢用‘侵占水田’这个词,而是用‘妨害’水田管理和应用一词代替。”法官理锦回忆起今年一起典型的涉梯田排除妨害类纠纷案时,眉头微蹙,眼底情绪有些复杂。
原、被告水田上下相连,被告家水田在上方,原告家水田在下方,中间以田埂为界,被告家认为原告在梯田清理杂草过程中,向田埂内里挖深,以此来扩充水田面积,故此被告在原告家水田里修建田埂挡墙,双方引发矛盾。

案件现场勘察田埂挡墙图(元阳法院供图)。
理锦,云南省元阳县人民法院新街中心人民法庭庭长。据她讲述,该案共进行了4次现场勘验。第一次,现场测量挡墙长宽高;第二次,现场还原前因后果,但双方不接受调解;第三次,开庭前和执行部门碰头,现场勘验后评估执行难度,看如何有效解纷;第四次,开庭后又勘测现场,根据挡墙具体方位、数据等,还原整个客观事实辅助最终判决。
“首要保证双方利益无较大损失。被告私建挡墙,虽侵占到了原告水田,但实际有加固作用,惠及双方田埂。既然已投入价值,已修建部分就保持原状。最终判决,拆除尾部残余围墙,保留已建成的保护性围墙。”理锦表示。
法官坦言,调解得多了不难琢磨出一点:矛盾,往往是一个时间段的情绪叠加至爆发。过了那个阶段情绪便缓些,更易解纷。来法庭的村民心里多少会有拘束感,尤其是头一回接触诉讼的,更需要心理适应过程。

上下水田紧密相连,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里关系,就算有一时矛盾也会被无限绵延的农耕文明抹平。
“法”字有水,才具柔性,如同这里的梯田。正如一位陪同采访的法院资深干警所说:“被万千沟渠水缠绕供养的梯田是活着的、会呼吸的,也是会生长的。”
仔细研究哈尼梯田千年农耕文明,不难发现刻入农耕民族骨子里的追求公平正义的朴素价值观——木刻分水法、沟长制,这也为司法守护梯田遗产奠定了精神基础。
哈尼人自古有一套水资源分配法:刻木分水。由村寨德高望重者牵头,根据各村寨、各条沟渠所需灌溉梯田面积,约定每条沟渠应分用水量。刻木分水可保梯田不论位置高低、面积大小、丰欠水年都能得到有效灌溉。彰显了哈尼人追求公平正义的朴素价值观。

图为梯田木刻分水器及沟渠。
木刻分水,代表的是一种集体秩序,现已发展成完备的制度,在红河县人民法院“木刻分水调解室”里挂着梯田调解法,丝丝润人心:
道法自然定分,遵循客观规律查明案件事实
村规民约指引,利用当地公序良俗思想启发
乡贤智者规劝,邀请德高望重人士教育感化
多元组织联调,借力各类调解组织合力调解
谦让共赢止争,互谅互让和谐共赢解决争议
回访观护事了,调后回访巩固彻底案结事了
千年梯田农耕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一套集体无意识的村规民约“赶沟”,并世代沿习。村寨选出有声望、勤劳务实、责任心强的人作为“赶沟人”,负责疏通梯田沟渠、分配水量、修缮沟渠、维护木刻分水器、调解梯田用水纠纷等,以保证沟渠水能流进各家梯田。现如今已进化为成熟的“沟长制”。

图为巡视梯田沟渠状况的当地沟长。
李文才,元阳县新街镇土锅寨村沟长,60岁,一人负责的水沟有三公里多。“清早5点多起,每天巡视沟渠状况,一走就是7、8公里。”像他这样的沟长,仅在土锅寨全村就有11名。
哈尼人有句话:“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水资源在森林、村寨、梯田、水系中循环往复,即“四素同构”生态系统,这也是为什么梯田被称为“会呼吸的灌溉系统”。曾佳解释道,水是哈尼梯田的“命脉”,哈尼人将沟水分渠引入田中进行灌溉,因山水四季长流,梯田中可常年饱水,保证了稻谷的发育生长和丰收。守护好水系,就是守住了梯田的命脉,守住了哈尼人的“根”与“魂”。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鸣谢: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云南省元阳县人民法院、云南省红河县人民法院
出品人:张守增 周翔
监制:何江 张伟刚
统筹:丁珈 冼小堤
策划:杨书培
记者:杨书培丨摄影:杨书培丨制图:张明翠
编辑:杨书培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